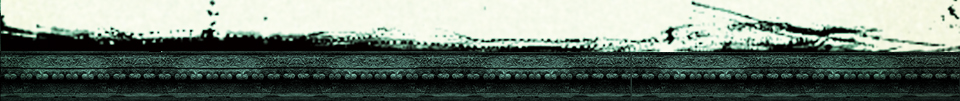|
贝家在苏州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苏州着名的园林狮子林以前是贝家的产业,贝家拥有这个花园长达百年。在这座以石头闻名的庭院中时常穿梭着一个男孩游戏的身影,他就是以后行走在世界建筑丛林中的佼佼者,建筑师——贝聿铭。 狮子林的石头形状奇特,凹凸有致,似乎一半是生命一半是石头。当时的园艺工人都是艺术家、雕塑家。他们看一眼石头就能找出可塑的地方,然后开始凿刻。他们会把原来的窟窿做大或凿些新的窟窿在上面,完全按其天然的形态和长势。然后将石头放到湖岸边,由水波的拍打完成这些作品。当水将石头磨得圆润,他们就把石头搬放在园子里,说:“这才是我们要的石头。”通常父辈们将石头放入水中,而由下一代将石头捞起。这是一种只存在于苏州当地的技艺,从这门技艺里,年幼的贝聿铭发现了时间对于一件艺术作品的重要性,这一发现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以后所有的设计。 “没有一件优秀的作品是在瞬间完成的,是可以不经历时间考验的。对建筑来说也是一样,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对它做出正确评价。所以我认为时间是很重要的,起码在我的工作中是这样的。” 中国的烙印 贝聿铭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到了17岁才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所以贝聿铭自己说过:“我还是中国人,虽然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我还是中国人,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看法。” 贝聿铭出生前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废除了皇位,中国正挣扎着寻找新的社会秩序。贝的祖父是一位典型的旧式文人,作为长孙,跟随着父亲居住在上海的贝聿铭,经常被祖父召唤回苏州老家,接受他带给贝聿铭的传统儒家理念的熏陶。 1920年,贝聿铭10岁时,父亲由香港迁至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主管。一个大都会,“东方的巴黎”就这样融进了贝聿铭的视野。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代表着时髦与浮华。有人说,没有比这里更紧张刺激的生活了。在这个所有人都能卷入的大旋涡里,富人可以更有钱,穷人可以做梦与祈祷。这是个摩天大楼与污水沟、阔太太与三轮车夫、凯迪拉克与牛车都兼而有之的城市。这个时候的贝聿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同学说从那时起,他就有说服别人的才能,而且他很善于推销自己,最适合当律师,没想到却成了一个建筑师。 周六周日,无所事事的贝聿铭会在桌球房消磨掉所有的时间。桌球房对面就是大光明戏院,不远处一栋新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那是闻名遐迩的国际饭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天天去看,越来越高,……23层高的建筑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件不可思议的大事,像在纽约建一个百层高的楼。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向往能建造这么高的建筑,也许当个建筑师。” 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216号的大光明戏院和60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贝聿铭的叔叔贝祖源回忆说,贝聿铭在那个时候就学会了用英文唱歌,在电影院里看最新的好莱坞电影,西方文化对上海青少年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就在上海,像贝聿铭这样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无法加入网球俱乐部,这对贝聿铭的内心造成了一种间接的压力,周围人对权势普遍的认同,也因此造就了他一生永无休止的雄心。 有梦想,也有野心,成功的故事就这样悄悄酝酿开来。 中学毕业后,贝聿铭面临着对未来前途的选择。他的父亲建议他从事金融业或者去学医,但贝聿铭太清楚父亲从事的职业有多么艰难,银行家的生活前景不能给贝聿铭带来一丝的快乐,在贝聿铭的心中真正令他好奇的唯有那栋建设中的大楼——国际饭店。“当时它是远东最高的建筑。听说国际饭店会盖26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每周六都要去看看它往上冒。” 贝聿铭说:“小时候看建筑物除了在上海看了一点高楼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对于我为什么走到建筑这条路,一半当然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有兴趣,一定是有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是到了美国才明白建筑是什么东西,因为在中国不大明了,在中国谈建筑,建筑是可以分3种。一个是在艺术方面的建筑,一个是在工程方面,就是结构方面的,也是建筑。做这种结构生意的人也是建筑,包商也是建筑,所以这3个都是不同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并不太明了,这个里面怎么分别,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3个大不相同,所以在艺术方面的路是我自己走的。” 不满18岁的贝聿铭背井离乡,远渡美国,开始他的建筑师生涯。“那时我第一次离家,而且是自己一个人……我以为我会动情,会落泪,结果完全不是那样。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幸运,能有机会去亲眼目睹一个新世界。”没有潸然泪下的惜别场面,贝聿铭对故乡的眷恋被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情绪所掩盖,那是他对未来的冒险,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好奇。 在美国贝聿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与企业大老板、艺术家和国家元首交情不浅,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西方人所能了解的。在他经历了太多的建筑和权力,移民和同化,美国式的奔放和中国化的收敛、顽固之后,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建筑。 贝聿铭年逾80,而他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在上海长大的中国人,了解、渗透进各个城市的内部,并在他的私人地图上填满东西。他从不循规蹈矩,总是试图在标新立异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也因其出色的现代感独具光彩。他长期积累的精湛技术和艺术修养透过他那双戴着黑边眼镜的眼睛穿透出来,冲破藩篱和整个时代。他均衡内心世界,阴和阳,上海和苏州,东方和西方,新和旧,种种这些正是他血液中的中国烙印所赋予的。 青春逼人的美利坚 来到美国之前,贝聿铭的视野仅仅局限于中国的东海岸,他是一个没见过太多世面的孩子。而美国之于他最初的印象则来自好莱坞的电影。 “我几乎从不错过巴斯特·基顿,查理·卓别林或平·克劳斯贝的电影。这也是我当时选择美国,而不是英国留学的原因。在我看来,美国的校园生活似乎充满了乐趣;我当时很年轻,希望过那种生活。” 虽然怀着一腔的热情和冲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在贝聿铭心中渐渐退去,留下的竟然是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他想念“姐妹、兄弟、父亲近况如何?”他总是给家人写去一封封信。在内心深处,贝聿铭总怀着一种责任感,一种深藏的中国式的家庭责任感。“我是来学习的,之后可以报效国家,我这一代的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爱国心,我想使中国变得富强,并为此出一份力。” 贝聿铭的满腔报国之志最终消散在战火硝烟里。1931年,日军入侵东北,1937年日军入侵上海,这是贝聿铭牢记至今的年份。后来爆发内战,读完麻省理工和哈佛之后的贝聿铭又产生了学成归国的念头,但父亲却阻止了他,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宝贵的忠告。 1935年,贝聿铭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但他很快受到学校古板的教学观念的打击,还没有正式开学就离开了那里。在对自己的绘画基础并不十分有把握的情况下,他来到波士顿报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学专业,系主任在贝聿铭学习一年后建议他考虑改学建筑。“我说我画画得不好那是废话,我不知道许多中国人不会画画。但这鼓励我去试一试。于是我试了,并且再没有回头。” 当时,欧洲正兴起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他们开始拒绝以往的繁冗复杂的概念,而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贝聿铭面对国际化的潮流,很难全部接受下来,因为他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直到后来他认识了建筑大师布劳耶,学到了“自由”的概念。 二战之时,包豪斯成为纳粹德国最早关闭的学府之一,建筑大师葛罗培斯因此来到了哈佛。当时的欧洲在建筑领域比美国先进得多,葛罗培斯带到哈佛的是将建筑与其他学科融会教育的包豪斯式的教学方式。他带来了马丁·华格纳教城市规划;拉兹洛·莫霍里·纳基教美术设计;马歇·布劳耶教建筑,名师云集的哈佛深深地吸引着贝聿铭。在贝聿铭的学习过程中,布劳耶教授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马歇·布劳耶提出光线对建筑是最重要的。他是太阳的崇拜者,他认为太阳的光芒使得建筑有了生命。贝聿铭回忆说:“我学习他的建筑,我学习他用建筑为人服务,为使用这个建筑的人服务,以及为什么做出这种设计的。我跟他有深厚的友谊,并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他去世。对空间的强调和外形的注重是他的特色,他认为,光线对一个建筑来说是最重要的。” 1942年,贝聿铭与陆书华结为夫妻,他们在自己的第一个家里建造了小花园,规模虽小,却很有中国情调。花草使夫妇俩想起了中国,而贝聿铭对园艺的钟爱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贝聿铭在郊外有一栋房子,他常去那里,在大自然中劳动,他常砍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树木更好地成长、结果。人与自然相辅相成是贝聿铭与生俱来且源自中国的信念,大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帮助他弥补了故乡的失落感。 在贝聿铭结束了学业的时候,他和夫人来到欧洲。在欧洲,贝聿铭看了很多现代派的建筑,剩下的时间,大都在教堂里,所以他对法国教堂印象很深。贝聿铭记得:“它们总是很高,用石头来建造这么高大的建筑,非常壮观,那些近乎于达到极致的东西总是让我心动不已。建筑和结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觉得建筑师如果不能意识到结构所蕴藏的力量,就不可能有好的设计。我笃信这一点。同时这个职业教你学会观察,你的眼睛会教给你建筑的内涵。因此要学会去看去观察各个地方不同的事物。在学习前辈和杰出人士的优点之后要用亲身经历来丰富自己,然后生活就变得更加充实,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你了解它的历史和其他。” 中国人的雄心——中银大厦 贝聿铭一生的70多件作品无一例外地与金钱、权力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将外交手腕和设计的独特混合运用在香港中国银行、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70多件建筑身上。尽管有巴黎民众对卢浮宫改建的反对声浪以及波士顿保险公司建筑大楼窗户纷纷跌落街头的灾难事件,这些并没有影响贝聿铭跻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师的行列,他是现代主义风格迈向人性化的工具。他的知名度证明,不必借助过度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一样可以创造出绝妙的公共空间。他把自己设计的建筑比作自己的女儿:“就是这样,好像有人生了十几个女儿,哪个最好,我没办法回答,每一个都有她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她的挑战。” 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的中银大厦。中银大厦曾经是亚洲最高的建筑,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一种结构意识上的纯真,进而达到美学上的纯真。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词,它必须要代表“中国人的雄心”。 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 移交香山饭店后,贝聿铭撤出北京,住进香港的大都饭店。在那里喝酒时他告诉助手们,他的下一个项目是在香港的商业区边缘,离大都饭店只有几个街段的地方为中国银行造一幢有纪念意义的塔楼。贝聿铭接受这份业务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的高层银行家都受过西方教育,而且老于世故;香港的承包商和工程师成熟老练,在全世界都有竞争力;同时也是出于一种怀旧感。1918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创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当时贝聿铭才1岁。由于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银行现在要祖诒的儿子为香港分行设计建造一幢威严的新办公大楼,以表现一种乐观、和解的氛围。 香港似乎是可以让贝聿铭得心应手开展业务的地方。香港与贝聿铭本人一样,把新与旧、东方与西方合成为一体。香港是海外华人网络的枢纽,也是在文化和地理上通向祖国的大门。 20世纪80年代,由于诺尔曼·福斯特大胆创新,为香港汇丰银行设计了一幢高技术总部大楼,香港的建筑声誉才得到改善。福斯特的设计仿佛是在惹人注目的港口沿岸地面上停放了一艘宇宙飞船。 早在上海时,汇丰银行就开始与中国银行在建筑上大唱对台戏。几十年中,这两家银行争相建设日益气派的大楼,和对方一比高低。 由于香港在1997年要交还中国,贝聿铭所设计的新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楼必然要象征香港美好的未来前景。这幢建筑必须使福斯特的银行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的标志相形见绌,使香港着名的老公司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会继续繁荣昌盛。贝聿铭说,它应该代表“中国人民的抱负”。 福斯特那座里程碑似的大厦建在港湾边沿,位置显要,而且有庞大的10亿美元预算作后盾。贝聿铭可享受不到这些优势。他只得到1.3亿美元的资金,而且地皮面积小,环境荒凉,高架公路从三面把那里框死。更糟糕的是,二战时日军总部曾占领过这块地。许多香港人相信,那些受尽折磨的囚犯依然阴魂不散,在那一带作怪。 香港的港口和小山之间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四五十层高的摩天大楼。贝聿铭要想在如此不利的地皮上建造出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就必须把大楼造得出奇的高。他自己也承认,纯粹依靠垂直高度的表现手法与香山饭店深思熟虑的朴素风格相比,是“180度的大转弯”。问题是,香港每一街段所拥有的摩天大楼数目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贝聿铭承诺说:“银行大厦的西洋派头将不比任何其他建筑物逊色。香港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它有技术也有办法建筑一幢现代大楼。” 在传统的高层建筑中,大楼重量随楼层的增加而增加,楼越高,柱越粗。建筑师们给支撑建筑物重量的长方形框架绑上横向拉结条起稳定作用,防止大楼侧面发生摇摆。由于香港经常受台风袭击,其横向拉结条的标准是纽约的两倍。如果换一位不像贝聿铭那样敢于大胆创新的建筑师,在面临这种额外的负担和预算资金不充足的情况时,也许就满足于建造一幢标准的50层盒式楼。然而,诺尔曼·福斯特那幢大受赞扬的银行大厦就坐落在两个街段之外的地方,不可避免的竞争促使贝聿铭尝试一切建筑可能。 从香山饭店回美国后不久,贝聿铭请儿子山地把一根方形木杆沿纵向切开,做成四个三角扇面柱,再将顶端切成斜面,用橡皮带把柱子绑在一起。当贝聿铭滑动这些柱子,让它们互相分离时,在向上达到柱子四分之一高度的地方,一座体积逐渐缩小、带有壁阶的塔状物出现了;在达到一半高度和四分之三高度时又分别出现了第二和第三座塔状物。剩下的那根柱子继续向上升,形成金字塔般的顶点。山地说:“父亲喜欢在召集助手之前闭门思考问题。我觉得,上述构思在父亲头脑中已完全成形。” 贝聿铭把图纸和由那捆柱子发展成的模型放在一起给莱斯,后者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他从贝聿铭的建筑灵感中发现了一种新概念的萌芽。这种概念将用经济实惠的纵向空间框架取代使传统高层建筑不堪重负的造价昂贵的“I”型柱组合。合作者罗伯琛说:“聿铭非常有灵感。他对建筑物、对人、对所有的事物都有最根本的直觉。他经常无法用语言表达这些感觉,但你绝对可以信赖他对建筑的直觉。” 稳固高层建筑物的一个办法是把重量向边缘转移,这样大楼就可以像两腿叉开站立的水手那样经受风暴的袭击。罗伯琛做到了这一点,方法是每隔13层楼用预制件像晶体管天线一样把贝聿铭设计的塔楼横向加固。而那些斜构件使大楼纵向和横向的负荷全部转移到四根角柱上,本来要用来重复横向加固的钢材现在可以纵向运用了。罗伯琛说:“它代表了一种新型建筑,它使人们看到结构在建筑中的重要性,它提高了条柱的高度。” 为了强调在结构上可行在美学上同样可行,贝聿铭把每隔13层楼对塔楼进行加固的斜构件和横向桁架用红笔圈出。在贝聿铭看来“如果我们不把结构表现出来,这幢楼就不会显得舒适。” 在尊重历史方面,贝聿铭表现了恰如其分的儒家态度,但他并不总是对侵犯他职业生活的行为持欢迎态度。过去他经常开玩笑说,他没有通过纽约州建筑师执照考试中的现场规划部分,原因是他应用了“风水”原理。 风水之说在香港很盛行。用来安抚鬼神世界的神秘做法和迷信仪式极不和谐地和监测世界市场的高技术金融机构并驾齐驱,兴盛不已。 贝聿铭曾说:“我怎么能相信那些东西?尽管如此,风水是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是建筑的一部分。” 在设计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时,贝聿铭曾把一本关于风水的书交给他的一位助手,让后者根据风水规则评估设计图样。经过仔细研究后,这位助手向他报告了设计中存在的几处侵犯风水的地方。 在后来的某个场合贝聿铭解释说:“香港的华人是你能找到的最迷信的人。在那里,风水是另一种大生意。那里的风水先生好比这里的律师:他们无处不在,你不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寸步难行。我知道我会遇到麻烦,但我不能预料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中国银行是至少不会在公开场合容忍风水说法的客户,因为共产主义信条已经正式抛弃了鬼怪神学。尽管如此,在技术图纸的设计过程中,银行给贝聿铭发来电报,对建筑正面展现的众多加了框的巨型“X”深表关注。在中国,“X”意味着遭殃,部分的原因是已判罪的犯人脖子上带着牌子,上面写有已经打过叉的他们的名字。中国的高层银行官员本身并不见得相信风水,但他们担心,一旦大楼风水不好,就会影响储户和房客的积极性。好几笔香港房地产交易都是因为风水不好弄得不欢而散。贝聿铭回忆,“他们婉转地建议,也许我应再看看那些‘X’。我告诉他们,‘X’是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要撑起整座大楼。” 经过大量的研究,贝聿铭把分隔每13层都要应用的预制件的横向桁架隐藏起来,并十分精明地把露在外面的部分描述成一系列互相交叉的宝石——这种吉利的形象使银行家们大为高兴。同时,他把塔楼比作雨后春笋——中国传统中再生和希望的象征。贝聿铭说:“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谈到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希望大楼具有与荷花一样的资质。” 贝聿铭所运用的是香港能够理解的象征手法。他让他那幢闪闪发光的方形尖塔坐落在3层楼高的花岗岩地基上,那笨重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基座与上面轻巧的塔楼十分笨拙地联结在一起,但它达到了表现尊贵与实力的目的。贝聿铭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银行必须显得很安全。”贝聿铭原来想利用陡峭的地势,从大楼的一端引入喷泉水,再让水从另一端喷出。但根据风水的原则,这样做意味着失败。于是,贝聿铭决定在庞大的地基两侧设置两座倾斜式喷泉,以减轻周围车辆的噪音。 由于他的框架系统非常有效,贝聿铭得以按照比较拮据的预算在纽约和芝加哥之外的地方建造了世界最高建筑之一。即使算上附加的台风加固设备,银行大厦也比传统的高层建筑少用40%的钢材和25%的电焊接缝。中国银行大楼在1985年年中破土动工,以每4天盖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整座超级建筑结构在16个月内完成。1988年8月8日,标志着大楼空中进程完工的封顶典礼正式举行。200名来宾戴着塑料头盔,乘着缠满铁丝的施工用的电梯,来到70层高楼的顶部。那里,粗糙的水泥地板上已放好一根刻有100名工人名字的柱子,富有喜庆色彩的金黄色螺栓把柱子牢牢固定。当人们用缠有红带的铲子掀起一铲铲具有象征意义的水泥时,无数只彩色气球放了出去。他们喝了一桶清酒,点了香,吃烤乳猪。大家大开诺尔曼·福斯特设计的汇丰银行大厦的玩笑:在这么高的位置看下去,汇丰银行大厦就像底下一座玩具城里的装饰品一样毫无气势。 这次典礼的时间是精心选择的,因为“8”和粤语中表示发财的“发”字谐音。有些香港居民认为1988年8月8日是20世纪最吉利的日子。然而,即使贝聿铭他们对中国传统如此礼让三分也未能消除大楼邻居们的顽固看法。建筑师和客户所不屑一顾的风水先生把他们的观点告诉了新闻界:贝聿铭可以诗意地把大楼比喻成充满希望的春笋,但在他们眼里,大楼是一柄带有三角形尖刃的寒光四射的尖刀。 据说,大楼有些尖角是直指总督府邸的。总督卫奕信邀请贝聿铭夫妇去总督府做客。在坐下来吃午饭前,主人给贝聿铭他们看花园里新增的滑稽内容。卫奕信后来解释说:“由于在许多人眼里,总督府代表香港政府,我们在那个尖角和总督府中心位置之间的直线上种了两棵柳树,算是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柳树的形状柔和、圆润,对大楼刀一般的尖利角度起了缓冲作用。就这样,问题解决,皆大欢喜。” 超越法国人心智空间的艺术——卢浮宫金字塔 到现在贝聿铭最得意的就是在他64岁的时候被邀请到法国巴黎参加卢浮宫重建计划。当时有人提出质疑,贝聿铭行么?能承担得起这项重任吗?这个时候,贝聿铭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毕竟卢浮宫是令全球人向往的地方,也正是卢浮宫成为贝聿铭巩固巅峰地位的公开舞台。当法国总统密特朗选中贝聿铭,整个巴黎大吃一惊,尽管贝聿铭已经是声名卓着的建筑师。 山地说:“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我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他们的不满。指责这项建筑已经超出了法国人的心智空间,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破坏性十足的装置。法国的政客、建筑界也轮流起身攻击。 贝聿铭回忆:“我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舆论方面总是批评居多,我在巴黎做卢浮宫14年,可以说在舆论方面,跟巴黎的民众、法国的民众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差不多费了两年。免不了的。因为这个卢浮宫的问题是法国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巴黎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国宝。所以卢浮宫是国宝,很多人说是第一的国宝。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去的中国人,他们不了解,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的建筑师到法国来改我们法国的国宝?特别要问总统密特朗为什么,我们法国人自己可以做嘛。所以非但是建筑方面的问题,也是和政治联在一起的问题。” 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直坚决支持贝聿铭,但这并不能阻止法国人幻想着有一大块疤痕,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他们抨击贝聿铭形成了热烈的运动,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的口号。文化部长米奇·盖说金字塔是一颗寒碜的钻石。他们形容这比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英国人占领巴黎,企图从卢浮宫拿走拿破仑征服欧洲时掠夺的艺术品的暴行,更令法国人愤怒。 贝聿铭始终信奉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我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旁人普通人接受不接受对于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接受不接受这个比较重要一点。总而言之,我的主观当然是免不了的,觉得应该要做的,觉得是对的。客观怎么看,这个我不知道,要等历史方面,再过几十年看看旁的人批评,历史最要紧,批评最重要的是历史,是要有一点时间。你不能说今天做了明天怎么不好,这个评价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身为法国往日光荣的象征,卢浮宫的历史就是法国的历史,它的象征意义远远不是其他建筑所能比拟的,法国评论家说:“擦擦眼睛,你以为是在做梦,好像回到了远古的古堡时代。怎么能允许让一个中国人修一个吓人的金字塔,这是对法国国家风格的严重威胁。”这段时间里的评论针对贝聿铭和他的设计,强烈的阵势使他几乎难以承受。 贝聿铭用他表面上无所谓的态度承受着他建筑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贝聿铭的助手说:“我从不记得贝聿铭曾经沮丧过,他认为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作品是整个设计的印象,他是位非常冷静的人,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同样保持着那独有的迷人微笑。”贝聿铭像许多了不起的人一样,什么时候都显得非常平和,而且不受外界强大压力的影响。 1988年,金字塔带来的横祸转变成为贝聿铭和他的支持者的最大喜悦,喜欢争吵同样喜欢意见一致的法国人接受了贝聿铭。这年3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新建成的金字塔里授予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令法国人难堪的是曾经极力反对的金字塔成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骄傲。说贝聿铭把过去和现在的时代精神的距离缩到了最小,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 贝聿铭说:“我当然真心希望人们喜欢我的作品,但是那些作品的持久性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一度像一个被放逐者的贝聿铭,神圣地走在一群仰慕他的人群中。金字塔落成的那天,记者采访他时,他的脸亮得像金字塔,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从来以谦恭姿态出现的贝聿铭这样评价金字塔:金字塔和巴黎的夜空一样,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美国的移民一般都会迷失在不同的文化中,最后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只有中国人例外。身为一个文化缝隙中的优雅摆渡者,贝聿铭可以说是鱼和熊掌兼得的人,当往事成为贝聿铭在美国的绊脚石时,他吸收西方最高级的事物,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他与海外华人维持联系,经常光顾中国城,喜欢吃毛蟹、凤爪和鸭舌头。了解他以后就会发现他和他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有人说贝聿铭的耐心、他的体态、他的精力、他的习性与魅力以及他眼睛里都闪耀着光芒。他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贝聿铭说,我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他只做他认为美丽的事,那就是创造出令人震惊的美感。 |